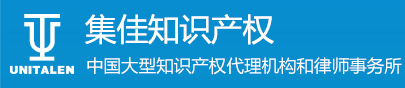文/北京市集佳律師事務所 戈曉美
2020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商業秘密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商業秘密規定》或“本規定”)開始施行。
《商業秘密規定》是一部單獨針對商業秘密民事案件中的法律適用制定的司法解釋,是對2007年2月《最高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07年《反法解釋》)中有關商業秘密的規定的吸收、整合和完善,也是對于2019年4月《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次修訂中商業秘密保護相關規定的修改的配套指引。全文共29條,涉及商業秘密的保護客體、商業秘密的構成要件、侵權判斷、侵權責任、訴訟程序及新舊法律適用問題共六個方面。
筆者在此結合多年處理商業秘密糾紛案件的司法實踐對該規定進行導讀。
第一部分(1-2條):商業秘密的保護客體
商業秘密的保護客體包括技術信息、經營信息等商業信息。
本規定第1條第1-2款分別對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進行了列舉。值得注意的是,本規定強調了對于算法、數據、計算機程序及其有關文檔的保護,且與技術有關的數據可以構成技術信息,與經營活動有關的數據可以構成經營信息,這凸顯了在大數據時代對于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保護。
其次,司法實務中關于“客戶信息”是否符合商業秘密構成要件存在較大爭議。本規定第1條第3款對客戶信息從正面進行了界定:客戶信息包括客戶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以及交易習慣、意向、內容等信息,第2條又從反面和消極的角度對“僅以與特定客戶保持長期穩定交易關系”從商業秘密保護范圍中予以排除。相比于07年《反法解釋》第13條有關客戶名單的規定,本規定雖然在措辭上有調整,但其內涵實質上是一致的。
第二部分(3-7條):商業秘密的構成要件
商業秘密的三大構成要件為:不為公眾所知悉、相應的保密措施、具有商業價值。
關于“不為公眾所知悉”要件,本規定第3條明確了判斷是否 “不為公眾所知悉”的時間節點:即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不為公眾所知悉”的兩大構成要素為:“不為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第4條從反面規定了可以認定為“為公眾所知悉”的五種具體情形。需要注意的是,對公知信息進行整理、改進、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仍有可能構成商業秘密。
關于“不為公眾所知悉”要件,本規定第3條明確了判斷是否 “不為公眾所知悉”的時間節點:即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不為公眾所知悉”的兩大構成要素為:“不為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第4條從反面規定了可以認定為“為公眾所知悉”的五種具體情形。需要注意的是,對公知信息進行整理、改進、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仍有可能構成商業秘密。
關于“商業價值”要件,本規定第7條首次提出所謂的“商業價值”需為因不為公眾所知悉而具有的商業價值,并且強調了生產經營活動中形成的階段性成果也可以認定為具有商業價值。
第三部分(8-14條):商業秘密侵權判斷
該部分對2019年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及第三十二條關于侵權行為的認定及舉證責任的分配進一步細化。
第8條規定了以違反法律規定或者公認的商業道德的方式獲取商業秘密的,應當認定為《反法》第九條第(一)項所稱的“以不正當手段獲取商業秘密”;
第9條規定了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直接使用、或修改、改進后使用,或根據商業秘密調整、優化、改進有關生產經營活動的,應當認定為《反法》第九條第(二)項所稱的“使用商業秘密”;
第10條規定了根據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所承擔的保密義務,以及未在合同中約定但根據誠信原則及合同的性質、目的、締約過程、交易習慣等,被訴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獲取的信息屬于商業秘密的,應當認定為《反法》第九條第(三)、(四)項中所稱的“承擔保密義務”。
第11條明確了可認定為《反法》第九條第三款所稱的“員工、前員工”的范疇:法人、非法人組織的經營、管理人員以及具有勞動關系的其他人員。
第12條規定了認定《反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所稱的“有渠道或者有機會獲取權利人商業秘密”的考量因素,包括:職務、職責、權限;承擔的本職工作或者單位分配的任務;參與和商業秘密有關的生產經營活動的具體情形;是否保管、使用、存儲、復制、控制或者以其他方式接觸、獲取商業秘密及其載體;及需要考慮的其他因素。
第13條規定了認定《反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所稱的“被訴侵權信息與商業秘密實質上相同”的考量因素,包括被訴侵權信息與商業秘密的異同程度;所述領域相關人員在侵權行為發生時是否容易想到該區別;被訴侵權信息與商業秘密的用途、使用方式、目的、效果等是否具有實質性差異;公有領域中與商業秘密相關信息的情況,以及需要考慮的其他因素。
第14條規定了侵權抗辯事由:自行開發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獲得被訴侵權信息的,不屬于侵權行為,該條與07年《反法解釋》第12條的規定保持一致。
第四部分(15-20條):侵權責任
第15條是關于商業秘密侵權案件行為保全的規定。與其他知識產權類型的案件相比,商業秘密的權利外觀是不確定的,保護范圍的確定也更具難度,各地法院對于商業秘密案件的禁令的態度較為保守。但鑒于商業秘密一經披露即永久喪失的特點,商業秘密侵權糾紛中的行為保全措施更具有重要意義。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關于審理知識產權糾紛行為保全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條亦明確了商業秘密侵權糾紛案件在滿足特定條件時也可適用行為保全。
第16條是關于商業秘密侵權責任主體的規定:經營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侵犯商業秘密的,視為商業秘密侵權。
第17條是關于停止侵害的時間期限的規定:一般應當持續到該商業秘密已為公眾所知悉時為止,也可以判決侵權人在一定期限或者范圍內停止使用該商業秘密。該條規定與07年《反法解釋》第16條的規定保持一致。
第18條是關于判決侵權人返還或者銷毀商業秘密載體,清除商業秘密信息的規定,以減少、消除再次侵權的風險。
第19條是關于因侵權行為導致商業秘密公開的賠償數額的確定,該條文與07年《司法解釋》第16條規定保持一致。
第20條規定了可參照許可使用費確定因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并規定了與之相關的考慮因素。2019年《反法》第十七條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法定賠償數額為500萬元,本條亦結合商業秘密的特點規定了適用法定賠償確定侵權數額的考量因素。
第五部分 (21-27條):訴訟程序
第21條是關于商業秘密訴訟程序中對于商業秘密證據材料采取必要保密措施的規定,以防止二次泄密。
第22、23、25條是關于處理商業秘密民刑交叉案件的相關規定,該部分對于處理民刑交叉案件時審理程序的先后問題及既判力問題作出了規定:第22條明確了民事訴訟程序中可申請調查收集刑事程序中形成的證據;第23條規定了可依據生效刑事裁判認定的實際損失或違法所得確定民事案件賠償數額;第25條明確了必須以刑事案件審理結果為依據的案件,遵循先刑后民的處理程序:中止民事案件的審理;該規定與2019年11月最高院引發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130條的規定相一致。
第24條規定了商業秘密糾紛案件中賠償證據妨礙制度的適用,該規定與2016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7條的規定相類似。
第26條是關于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提起訴訟的相關規定,該規定與07年《反法解釋》第15條的規定一致。
第27條是關于明確所主張的商業秘密具體內容的規定:權利人應當在一審法庭辯論結束前予以明確,在二審中另行主張一審未明確的商業秘密具體人內容的,二審法院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雙方均同意由二審法院一并審理的,可以一并審理。
第六部分(28-29條):新舊法律的適用
《反不正當競爭法》自1993年施行以來,先后經歷了2017年和2019年兩次修訂。本規定第28、29條明確了新舊法律的適用以侵權行為發生時為基準,被訴侵權行為在法律修改前發生且持續到修法之后的,適用修改后的法律;正在審理的一審、二審案件適用本規定;施行前已經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不適用本規定再審。